全館即時榜
-
- 特價
受保護的內容: 訂閱《經典雜誌》一年12 期+3期(菁英訂戶訂購方案)
-
NT$2,640NT$2,000
-
- 特價
出世心,入世行 ——靜思精舍的日常
-
NT$360NT$324
編輯推薦
描述
透過戰爭能將局勢改變,卻也衍生新的問題,這是任誰也意料不及與無法操縱的。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於國共內戰中戰事失利,帶著約一百二十萬軍民遷臺;然卻有孤軍一支,游擊於比臺灣面積大三倍的泰緬邊境,力圖反攻雲南,堅持收歸故土。他們歷經祖國邊境的夾殺、無數袍澤戰死、不知為誰而戰的掙扎,最終落腳泰國北部六個府七萬平方公里的邊境高山。七萬餘華人軍民在異域墾荒,也在一個個山頭上,建立起近百個難民村。
從流亡無立錐之地,逐漸到身分被泰國政府認同;從不毛之地刻苦求生,到外援進入協助自立。數十年來他們從為國家而戰,到為生存而戰,異域終成後代子孫的新故鄉。
一九九五年起,慈濟接續中華救助總會在泰北難民村的援助工作,擬定「泰北三年扶困計畫」,援助項目包括重建難民村、負擔帕黨與熱水塘兩所老兵安養中心費用,並提供農業輔導、貧戶醫療濟助與教育援助。
「唯有靠有步驟、有方法的援助計畫才能有具體成效。」一九九一年的華中、華東水患,奠定了慈濟海外賑災的基石。有了直接、重點、尊重的原則外,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王端正表示:「泰北的苦難不是因為天災而起,而是長期戰亂引起的問題。這次不只是急難救助,我們還要有計畫、有配套與延續性,好好地利用三年的時間做好。」泰北三年扶困計畫也因此成為慈濟基金會,從急難救助發展到長期援助成功的案例;也奠定了慈濟志業在泰國開枝展業,融合人文、扎根當地。
目錄
〈序〉泰北的蛻變與重生 王端正
【漂泊異鄉】
走訪異域
游擊邊境
孤注一擲
悲寂殘生
舞草低語
每月送暖
踩地造村
罌粟花開
【落地生根】
救總伸援
農業輔導
軍軍相惜
溫暖守護
愛不間斷
安居安身
打造出路
生根深耕
綠色金礦
【扎根教育】
克難辦學
建校波折
扎根希望
師有妙法
心靈豐收
語文優勢
【否極泰來】
認養計畫
來臺取經
愛是良藥
神祕配方
責無旁貸
回饋之旅
【採訪後記】看見天明
【泰國慈濟志業大事紀】
【參考書目】
推薦專文
【序】
泰北的蛻變與重生
◎王端正(慈濟基金會副總執行長)
很慶幸我們見證到了,也參與了一段既鮮明又滄桑的歷史,那是從困頓到坦途,從黑暗到光明,從顛沛流離到安樂定居的戰亂轉折歷史,在這戰亂轉折史中,「慈濟泰北扶困計畫」也發揮了不小的影響力,產生了不少動人的美麗浪花。
「慈濟泰北扶困計畫」,雖說是從一九九五年開始實施到一九九八年結束,但事實上,早在該計畫實施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就開始了實地踏訪與周詳籌畫的工作了。歲月如矢,轉眼間也已十九年。
十九年前為了擬定慈濟泰北扶困計畫,曾前後兩次深入泰北山區,實地了解泰北居民的生活情形與所處的艱難環境,慈濟就與泰北山區結下不解之緣。
當時,明知雨季已開始,還是抓緊時間拜訪難民村,好幾次人車無法順利而行,甚至困在山區差點動彈不得。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碰上大雷雨,視線不清,車子只能緩緩前行,一行人的心在車內糾結著;因為滿嘎拉村發高燒小男孩縮在茅草房竹床上的身影,揮之不去。
無醫可看,無藥可用,只能靠自身免疫力來面對疾病,這不僅是一個孩子的苦難示現,更是整個難民村實際困境的縮影。
重建村落只是泰北扶困計畫的起步,接下來還有農業改良及農業技術的推廣與傳授,以及清寒績優學生獎助學金的設立,這些計畫同時含蓋清萊、清邁。正所謂安居才能樂業,安身才能立命,身心安頓才能開創未來的命運。
十九年來,慈濟一直沒有離開泰北,慈濟人一直見證著泰北枯榮與新生;十九年來,慈濟人不僅沒有離開泰北,還在泰北興學辦校,為泰北的未來打造更亮麗的希望。現在的泰北,山還是山,水還是水,但人已不是當年的人,事已不是當年的事了。
慈濟當年所建的新村,依然屹立;所輔導種植的茶園依然翠綠,為育苗所暫時管理的農場依然運作;所幫助的學生已經成人成才;所陪伴的老兵已經逐漸凋零,但所立的碑石依然在目,碑文依然清晰可讀。
這不禁讓我想起孟浩然的一首詩: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孟浩然是誰?是唐代的大詩人。這位大詩人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登上了位於現在湖北襄陽縣南的峴山,看見了晉朝羊祜治理襄陽時普施德政,老百姓為了感念他的仁德,在峴山建碑永誌,凡來此登臨的人,看見了羊公碑,讀罷了碑文上的記載,無不感動流淚,所以羊公碑又稱墮淚碑。詩人總是多愁善感,孟浩然看見了羊公碑,讀罷了碑文,也感動得淚流滿面,引發了諸多感觸,於是寫下了這首傳誦千古之作。
歷史告訴我們,社會國家未來是否有前途,就要看現在教育是否成功;換句話說國家的興亡,繫於教育的成敗,為了給泰北孩子一個很好的教育機會,也為了給泰北社會一個很好的未來發展,證嚴上人決定投入心力,在泰北興辦學校,從事教育志業。
當時我們決定要在芳縣蓋學校時,有不少人提出不同的意見,認為這麼好的學校應該要蓋在都市,都市人口多,學生來源比較沒有問題。但在泰北蓋學校是扶困計畫的延續,更何況上人認為偏遠貧困地方的孩子,更應該要給予應有的教育;不僅要給於應有的教育機會,更應該用心投入更多的資源。
或許有人看過《異域》這本書,對泰北殘兵敗將,困守綿延深山的悲情,留下顯明印象;也或許有人對當年「送炭到泰北」的新聞報導,還有些鮮活的記憶,當時都會對進退維谷的所謂「亞細亞的孤兒」給予無限的同情,對他們艱難處境,都曾一掬同情的眼淚。但漫漫歲月過去了,誰還復問那些老兵的存亡與狀況呢?
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這些孤憤的老兵,不僅都已經垂垂老矣,而且正在迅速凋零;當年「亞細亞孤兒」所引起的震撼與反思,正在走入歷史;國共對抗的浪潮也正趨波平浪靜。然而我們是否真的能夠以歷史為鏡嗎?歷史這面鏡子真的能讓人知興替,明得失嗎?事實證明:個人的愛恨情仇,即使面對歷史這面鏡子,也會像是霧看花,豈能看出歷史的興替與個人的得失!豈能看出道理的究竟與事實的真相!
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名將麥克‧阿瑟在美國作證時說:「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凋零的是他們的身軀,不死的是他們的精神。只要不讓青史盡成灰,老兵的精神與其所象徵的意義,就會在歷史長河不斷迴盪。
二○一二年六月重返泰北之行,心情既澎拜又惆悵,既期待又感傷。
澎拜的是:青山綿延,孤憤處處,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與愛恨情仇,不斷悲壯上演,也不斷落寞謝幕。困頓的歷史小浪花與順境的歷史大漣漪,匯聚成壯闊的史詩,這怎能不令人心情澎湃?
惆悵的是:江山依舊,人事全非,當年把手話烽火的老兵與難民,被無情歲月浪潮一一淘盡了,他們的豪邁笑容與濃濃鄉音,只能空留回憶。
期待與感傷的是:十九年前的幼苗茁壯了,歲月可以淘盡上一代,卻不能淹沒第二代,第三代,這就是「新陳代謝」的真正意涵。懷念第一代的悲壯,更期待樂見第二代、第三代的蛻變與展翅。當我們目睹泰北難民與老兵的後代,能破繭而出,再創自己的輝煌,心中既喜悅又感傷。
當時年僅四、五歲「不識人間愁滋味」的稚氣女兒,現在已亭亭玉立大學畢業,成為社會菁英了。當年的玩伴,有的已走出山區,投入都市的人海;有的已成家立業,繼續在泰北那塊養活他們的土地上,勤耕反饋;有的已遠嫁美國,經營她的美國夢;有的則往來大陸與臺灣之間,從事商貿活動。
上一代的恩恩怨怨,似乎沒有在他們的心中留下陰影;過去的煙硝戰火與漫天風雲,似乎已雲淡風輕了。
現在泰北山區在一片發展觀光聲中,有了全新的思維與全方位的發展。當年的「作戰指揮部」,現在變成民宿客棧了;當年滿山遍野的罌粟花海,現在已發展成觀光茶園了;泰國皇家基金會經營的花博農場,已大放異彩了;果園果實累累,鮮紅荔枝,讓人垂涎;碩大芒果,讓人嘴饞。
站在山崗眺望,層巒疊翠,江山是如此美好,泰北不復是當年劍拔弩張的泰北了;氣氛也不復是當年肅殺悲壯的氣氛了,武裝減少了,觀光客增加了,一片祥和正導引著泰北朝欣欣向榮的歷史轉折邁進,這是泰北之幸,也是十九年來慈濟泰北扶困計畫最想看到的結果。
【採訪後記】
看見天明
◎凃心怡
一顆或許已經殞落的星,卻因為距離、時間的交錯,在我眼前閃耀著光暉;幾百萬年前的星體,將它們發光發熱的生命奉獻於此刻。
「你想告訴我什麼?」逐漸探索異域孤軍的故事,十多年前對著夜空問過的話,又再度從口中傾吐,只是這回不再懷著年少浪漫情懷,複雜的情緒幾度讓人泫然欲泣。
那是在泰北的義民文史館。黃色的屋簷、紅色的梁柱,標準的中國式建築分左廊、右廊與中殿。左廊上,一禎禎的黑白照片搭配淺顯文字,僅僅十餘幅就走完那段艱苦的歲月,不捨與遺憾的情緒交錯在心中。
腳步隨著廊道踏入中殿,突然間,我無法再移動雙腳。數百座朱紅牌位,排排列放令人鼻酸,但令人湧出淚水的,是毫無掛飾的白牆上以紅色顏料大大漆寫的那四個字——精忠報國。這四個字宛如沈重的槍枝,壓在他們的牌位上、肩頭上,直到人去魂散。
若要以一種植物來形容泰北孤軍,我想非曼陀羅花莫屬了。曼陀羅花又名醉仙花、狗核桃、瘋茄兒等,別名高達八種;孤軍因為定位複雜,對泰、緬、寮等國而言,到底是盟友還是敵人?曼陀羅花含毒,孤軍的強悍令各國望之膽怯,否則哪有兩次撤臺,又被重用抵禦泰共?
曼陀羅花潔白無暇,就如孤軍忠貞不二;曼陀羅花生命力強,泰北村落到處可見,就像孤軍自雲南一路撤走,至今在泰北安然茁壯。
自泰北返臺,我將一個月的採訪濃縮至一萬餘字刊載在第五百五十一期《慈濟月刊》。出刊後不久,接到一通來自屏東讀者的電話。
電話那端有著濃厚的鄉音,對方自我介紹,今年八十二歲,空軍上校退役,「看了你的文章,我內心有許多感觸。民國五十年第二次撤臺,我就是開飛機去泰北接那群人回來的其中一個。」
幾日後,我與他——許浩然老先生,約在屏東見面。
雖然上了年紀,許浩然一頭未曾染過的髮絲依舊烏黑,腳步相當穩健,開車當然也行。坐上車,他便開始談起那次撤臺任務。
「接運孤軍返臺的行動定名為『國雷演習』,又稱『旋風計畫』。」許浩然說,這一趟任務雖是國際的決定,但並不保障安危,為避免中途遭中共派機攔截,空運機隊都是在黃昏或黑夜起飛,先繞過海南島外圍,從南越控制區北端的順化上岸,再經過寮國領空飛向泰國清邁。
「十小時不著陸的長途飛行,對我們來說不僅是首次,在國際間也不多見。而先遣小組在當地機場只建通訊電臺,並無助航及夜航設備,因此飛行員都必須靠目視。」許浩然回憶,當時除了天上的星、空中的雲以及茫茫無邊的海,根本沒有任何標示可以作為飛行參考。
許浩然曾打過八二三砲戰,也參與過越戰,對於這次航程抱持嚴謹態度,卻也信心滿滿。「在屏東的機場準備出發時,燈火通明,車輛不停奔駛、加油、試車與檢查,雖然大家都很忙碌,卻帶著興奮的笑容,好像在辦喜事一樣。」他笑了一笑,自問自答,「不是嗎?大家都在等著迎接祖國兒女的歸來。」
最後,許浩然運駛的飛機,低空通過清邁機場上空,平穩地降落在跑道上。在異國土地上,首先印入眼簾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接著看見以樹叢編織的竹棚下,男女老幼人人引頸期盼。
「他們就是要撤回臺灣的孤軍和家眷,電影異域曾演到接機那一幕,人人搶著上飛機。」許浩然大氣一吐,「那是電影效果,實際上他們都相當有秩序。」
說著,許浩然的車進入屏東縣的里港鄉,他介紹八十七歲的陳訓民給我認識,直說:「他就是當年我們載回來的那一批人之一,這的上校就他一個,是素質最高的!」
陳訓民身材高大,拿著一疊黑白老照片。照片中,國軍挺起胸膛,衣衫整齊,井然有序地列隊行走,領隊者掌旗,那是一面國旗。「這是我們剛下飛機時。撤臺大約有四千多人,先是降落在屏東,之後再送我們到高雄鳳山的中正預校集中。」
他再翻出一張照片,畫面中大家圍著一圈小凳子,飯菜就放在地上,「第二天我們就坐火車到成功嶺,這是在成功嶺用餐的畫面。」陳訓民齡老智不衰,還記得在成功嶺居住的那一、兩個月吃過的飯菜,「有豆腐乾炒韭菜、炒空心菜,最高等的就是豬腳黃豆!」
在成功嶺都做些什麼呢?陳訓民說他們在等待並做決定,「想繼續留下來服役的就當兵,不願意的就歸化義民,政府找好土地、蓋好房子才將我們從成功嶺遷出去。」
陳訓民選擇繼續服役,他的太太則回歸平民生活,並落腳里港。
屏東縣的里港與高雄市的美濃雖分處不同縣市,但以地理位置來看則是連成一氣,這群泰國歸來的義民被分配到兩地四個部落,分別是信國、定遠、成功與精忠。
有別於成功嶺令他難忘的飯菜,來到里港,陳訓民開始後悔了。「像河床一樣全是石頭!一根草也沒有,一棵樹也沒有,每天起床就是在搬石頭整地,實實在在是在墾荒。」
之後,我又拜訪國軍第二代魯平安,雖然遷臺時他不過幾個月大,但對從小居住的地理歷史很是了解。
魯平安說,他們定遠部落這一塊地的北方住著客家人,南邊則是本省人,「我們這塊地是河床地,也是有土,但大部分是石頭和沙子,什麼也種不出來,是客家人跟本省人不要的地。」墾荒期來來去去也耗盡一年半載,大夥兒的皮膚都被曬得黑亮,「所以本省人都叫我們黑人,說我們是黑人村莊。」
魯平安領我看一張村莊早期的老照片,指著兩戶人家中間的圍牆要我細看,「看,連圍牆都是用石頭砌的,就地取材呀!」
石頭搬完之後,政府自外縣市運土過來,幫他們填入三十公分深的土,並發予幾株芒果苗,但拿槍比拿鋤頭在行的他們,哪懂得耕種?「苗很快就死了,有點交際手腕的人去跟本省人打好關係,跟他們學,學了之後再回來教村民。」
「當時大家都覺得很懊悔——怎麼回來臺灣,日子一樣難過?」魯平安說,當時最讓他們痛苦的不只是環境困難,還有省籍歧視。
孤軍在泰北時,不僅要面對戰爭的危險、環境的險惡,身分不合法的他們還被冠上入侵者的頭銜;然而回到臺灣,他們雖然免去戰爭之苦,但同樣得面對戰後的困頓環境,且無法取得當地人的認同。無論在泰北或是臺灣,他們都像是外人。
一九九○年,政府依榮民退輔政策放領土地,他們墾出的荒地終於成為一張自有地契,再加上臺灣經濟連三跳,牽動土地價格飛揚,魯平安表示:「剛放領時,一分地值三十萬,之後曾衝到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萬,現在平均價格是八十萬。」
隨著局勢更迭變化,地價增值、政府的照顧,和孩子們的教育普及,讓這群曾懊悔到臺灣的人,漸漸地定下心來。陳訓民回想來臺這四十幾個年頭,對於回臺的決定感到萬幸,「隨著生活愈來愈穩定,我們都覺得回來是對的。」
走訪泰北與里港,我有一種感覺——這群背景相同的人們,並沒有因分處兩地而發展出不同人生,他們的奮鬥、求生與爭取,到如今擁有安定生活,過程都是同樣艱辛。
這一段歷史雖然有著許多悲傷故事,但令人深感慶幸的是,隨著時間的消逝,已逐漸輕盈。
相關推薦
-
- 特價
受保護的內容: 訂閱《經典雜誌》一年12 期+3期(菁英訂戶訂購方案)
-
NT$2,640NT$2,000
-
- 特價
出世心,入世行 ——靜思精舍的日常
-
NT$360NT$3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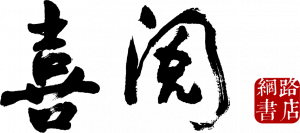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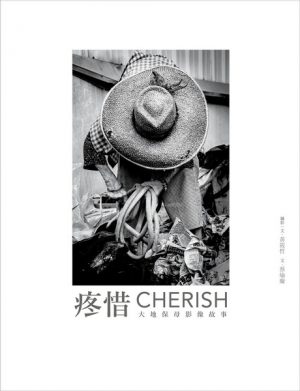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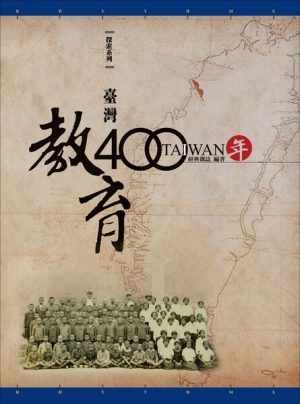
商品評價
目前沒有評價。